徵征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是台中南屯變更登記會計服務推薦最佳稅務後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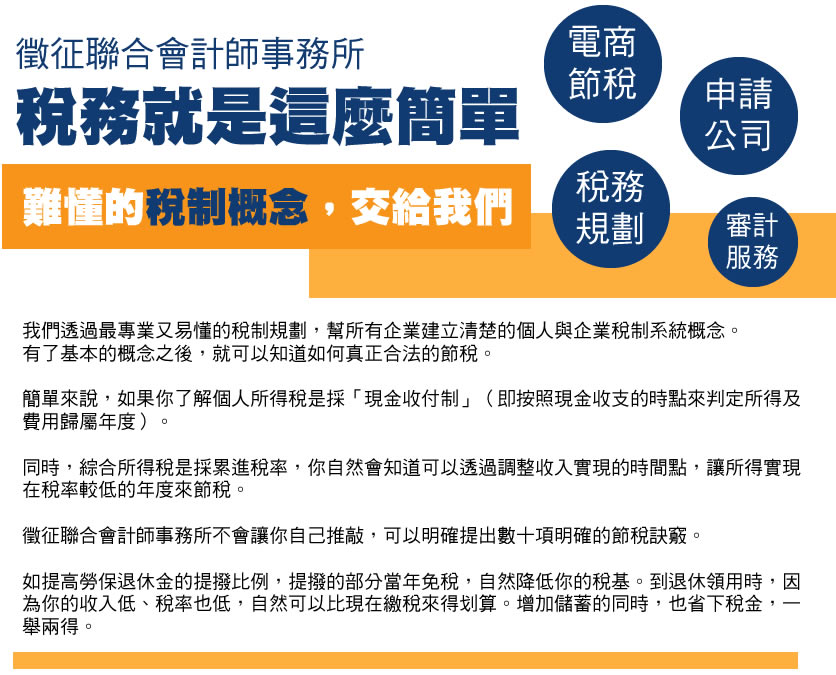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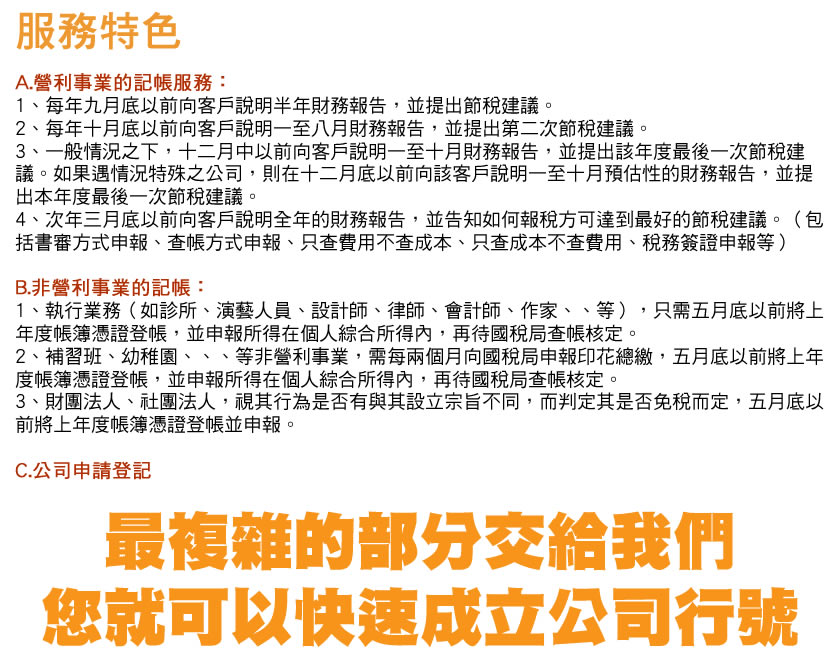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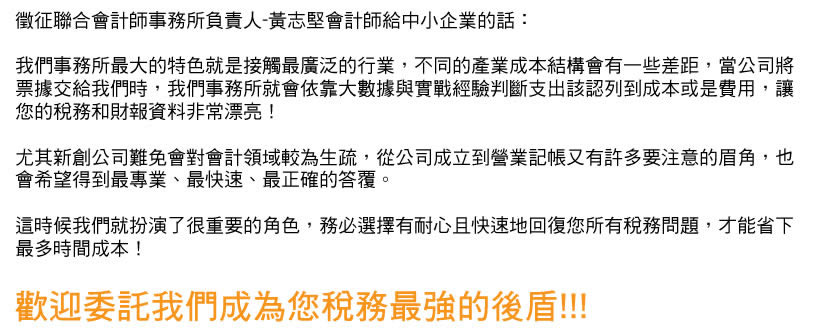
台中豐原稅務帳務會計師事務所, 台中國際租稅諮詢, 台中南屯稅務及電子商務規劃
朱自清:說話 誰能不說話,除了啞子?有人這個時候說,那個時候不說。有人這個地方說,那個地方不說。有人跟這些人說,不跟那些人說。有人多說,有人少說。有人愛說,有人不愛說。啞子雖然不說,卻也有那伊伊呀呀的聲音,指指點點的手勢。 說話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天天說話,不見得就會說話;許多人說了一輩子話,沒有說好過幾句話。所謂“辯士的舌鋒”、“三寸不爛之舌”等贊詞,正是物稀為貴的證據;文人們講究“吐屬”,也是同樣的道理。我們并不想做辯士,說客,文人,但是人生不外言動,除了動就只有言,所謂人情世故,一半兒是在說話里。古文《尚書》里說,“唯口,出好興戎,”一句話的影響有時是你料不到的,歷史和小說上有的是例子。 說話即使不比作文難,也決不比作文容易。有些人會說話不會作文,但也有些人會作文不會說話。說話像行云流水,不能夠一個字一個字推敲,因而不免有疏漏散漫的地方,不如作文的謹嚴。但那些行云流水般的自然,卻決非一般文章所及。——文章有能到這樣境界的,簡直當以說話論,不再是文章了。但是這是怎樣一個不易到的境界!我們的文章,哲學里雖有“用筆如舌”一個標準,古今有幾個人真能“用筆如舌”呢?不過文章不甚自然,還可成為功力一派,說話是不行的;說話若也有功力派,你想,那怕真夠瞧的! 說話到底有多少種,我說不上。約略分別:向大家演說,講解,乃至說書等是一種,會議是一種,公私談判是一種,法庭受審是一種,向新聞記者談話是一種;——這些可稱為正式的。朋友們的閑談也是一種,可稱為非正式的。正式的并不一定全要拉長了面孔,但是拉長了的時候多。這種話都是成片斷的,有時竟是先期預備好的。只有閑談,可以上下古今,來一個雜拌兒;說是雜拌兒,自然零零碎碎,成片段的是例外。閑談說不上預備,滿是將話搭話,隨機應變。說預備好了再去“閑”談,那豈不是個大笑話?這種種說話,大約都有一些公式,就是閑談也有——“天氣”常是閑談的發端,就是一例。但是公式是死的,不夠用的,神而明之還在乎人。會說的教你眉飛色舞,不會說的教你昏頭搭腦,即使是同一個意思,甚至同一句話。 中國人很早就講究說話。《左傳》,《國策》,《世說》是我們的三部說話的經典。一是外交辭令,一是縱橫家言,一是清談。你看他們的話多么婉轉如意,句句字字打進人心坎里。還有一部《紅樓夢》,里面的對話也極輕松,漂亮。此外漢代賈君房號為“語妙天下”,可惜留給我們的只有這一句贊詞;明代柳敬亭的說書極有大名,可惜我們也無從領略。近年來的新文學,將白話文歐化,從外國文中借用了許多活潑的,精細的表現,同時暗示我們將舊來有些表現重新咬嚼一番。這卻給我們的語言一種新風味,新(www.lz13.cn)力量。加以這些年說話的艱難,使一般報紙都變乖巧了,他們知道用側面的,反面的,夾縫里的表現了。這對于讀者是一種不容避免的好訓練;他們漸漸敏感起來了,只有敏感的人,才能體會那微妙的咬嚼的味兒。這時期說話的藝術確有了相當的進步。論說話藝術的文字,從前著名的似乎只有韓非的《說難》,那是一篇剖析入微的文字。現在我們卻已有了不少的精警之作,魯迅先生的《立論》就是的。這可以證明我所說的相當的進步了。 中國人對于說話的態度,最高的是忘言,但如禪宗“教”人“將嘴掛在墻上”,也還是免不了說話。其次是慎言,寡言,訥于言。這三樣又有分別:慎言是小心說話,小心說話自然就少說話,少說話少出錯兒。寡言是說話少,是一種深沉或貞靜的性格或品德。訥于言是說不出話,是一種渾厚誠實的性格或品德。這兩種多半是生成的。第三是修辭或辭令。至誠的君子,人格的力量照徹一切的陰暗,用不著多說話,說話也無須乎修飾。只知講究修飾,嘴邊天花亂墜,腹中矛戟森然,那是所謂小人;他太會修飾了,倒教人不信了。他的戲法總有讓人揭穿的一日。我們是介在兩者之間的平凡的人,沒有那偉大的魄力,可也不至于忘掉自己。只是不能無視世故人情,我們看時候,看地方,看人,在禮貌與趣味兩個條件之下,修飾我們的說話。這兒沒有力,只有機智;真正的力不是修飾所可得的。我們所能希望的只是:說得少,說得好。 朱自清作品_朱自清散文集 朱自清:擇偶記 朱自清:說夢分頁:123
郁達夫:楊梅燒酒 病了半年,足跡不曾出病房一步,新近起床,自然想上什么地方去走走。照新的說法,是去轉換轉換空氣;照舊的說來,也好去拔除拔除邪孽的不祥;總之久蟄思動,大約也是人之常情,更何況這氣候,這一個火熱的土王用事的氣候,實在在逼人不得不向海天空闊的地方去躲避一回。所以我首先想到的,是日本的溫泉地帶,北戴河,威海衛,青島,牯嶺等避暑的處所。但是衣衫檻褸, 饘粥不全的近半年來的經濟狀況,又不許我有這一種模仿普羅大家的闊綽的行為。尋思的結果,終覺得還是到杭州去好些;究竟是到杭州去的路費來得省一點,此外我并且還有一位舊友在那里住著,此去也好去看他一看,在燈昏灑滿的街頭,也可以去和他敘一敘七八年不見的舊離。 像這樣決心以后的第二天午后,我已經在湖上的一家小飯館里和這位多年不見的老朋友在吃應時的楊梅燒酒了。 屋外頭是同在赤道直下的地點似的伏里的陽光,湖面上滿泛著微溫的泥水和從這些泥水里蒸發出來的略帶腥臭的汽層兒。大道上車夫也很少,來往的行人更是不多。飯館的灰塵積得很厚的許多桌子中間,也只坐有我們這兩位點菜要先問一問價錢的顧客。 他——我這一位舊友——和我已經有七八年不見了。說起來實在話也很長,總之,他是我在東京大學里念書時候的一位預科的級友。畢業之后,兩人東奔西走,各不往來,各不曉得各的住址,已經隔絕了七八年了。直到最近,似乎有一位不良少年,在假了我的名氏向各處募款,說:“某某病倒在上海了,現在被收留在上海的、個慈善團體的XX病院里。四海的仁人君子,諸大善士,無論和某某相識或不相識的,都希望惠賜若干,以救某某的死生的危急。”我這一位舊友,不知從什么地方,也聽到了這一個消息,在一個月前,居然也從他的血汗的收人里割出了兩塊錢來,慎重其事地匯寄到了上海的XX病院、在這XX病院內,我本來是有一位醫士認識的,所以兩禮拜前,他的那兩元義捐和一封很簡略的信終于由那一位醫士轉到了我的手里。接到了他這封信,并巨另外更發見了有幾處有我署名的未完稿件發表的事情之后.向遠近四處去一打聽,我才原原本本的曉得了那一位不良少年所作的在前面已經說過的把戲。而這一曲實在也是滑稽得很的小悲劇,現在卻終于成了我們兩個舊友的再見的基因。 他穿的是肩頭上有補綴的一件夏布長衫,進飯館之后,這件長衫卻被兩個紐扣吊起,掛上壁上去了。所以他和我都只剩了一件汗衫,一條短褲的野蠻形狀。當然他的那件汗衫比我的來得黑,而且背脊里已經有兩個小孔了,而我的一件哩,卻正是在上海動身以前剛花了五毫銀市新買的國貨。 他的相貌,非但同七八年前沒有絲毫的改變,就是同在東京初進大學預科的那一年,也還是一個樣兒。嘴底下的一簇繞腮胡,還是同十幾年前一樣,似乎是剛剃過了三兩大的樣子,長得正有一_二分厚,遠看過去,他的下巴像一個倒掛在那里的黑漆小木魚。說也奇怪,我和他同學了四五年,及回國之后又不見了七八年的中間,他的這一簇繞腮胡,總從沒有過長得較短一點或較長一點的時節。仿佛是他娘生他下地來的時候,這胡須就那么地生在那里,以后直到他死的時候,也不會發生變化似的。他的兩只似乎是哭了一陣之后的腫眼,也仍舊是同學生時代一樣,只是朦朧地在看著鼻尖,淡含著一味莫名其妙的笑影。額角仍舊是那么寬,顴骨仍舊是高得很,顴骨下的臉頰部仍舊是深深地陷人,窩里總有一個小酒杯好擺的樣子。他的年紀,也仍舊是同學生時代一樣,看起來,從二十五歲到五十二歲止的中間,無論哪一個年齡都可以看的。 當我從火車站下來,上離車站不遠的一個暑期英算補習學校——這學校也真是倒霉,簡直是像上海的專吃二房東飯的人家的兩間閣樓——里去看他的時候,他正在那里上課。一間黑漆漆的矮屋里,坐著八九個十四五歲的呆笨的小孩,眼睛呆呆的在注視著黑板。他老先生背轉了身,伸長了時時在起痙攣的手,盡在黑板上寫數學的公式和演題,屋子里聲息全無,只充滿著滴滴答答的他的粉筆的響聲。因此他那一個圓背和那件有一大塊被汗濕透的夏布長衫,就很惹起了我的注意。我在樓下向他們房東問他的名字的時候,他在樓上一定是聽見的,同時在這樣靜寂的授課中間,我的一步一步走上樓去的腳步聲,他總也不會不聽到的,當我上樓之后,他的學生全部向我注視的一層眼光,就可以證明,但是向來神經就似乎有點麻木的他,竟動也不動一動,仍在繼續著寫他的公式,所以我只好靜靜的在后一排學生的一個空位里坐落。他把公式演題在黑板上寫滿了,又從頭至尾的看了一遍,看有沒有寫錯,又朝黑板空咳了兩三聲,又把粉筆放下,將身上的粉未打了一打干凈、才慢慢的轉身來。這時候他的額上嘴上,已經盛滿了一顆顆的大汗,他的紅腫的兩眼,大約總也已滿被汗水封沒了吧,他竟沒有看到我而若無其事的又講了一陣,才宣告算學課畢,教學生們走向另一間矮屋里去聽講英文。樓上起了動搖,學生們爭先恐后的奔往隔壁的那間矮屋里去了,我才徐徐的立起身來,走近了他,把手伸出向他的粘濕的肩頭上拍了一拍。 “噢,你是幾時來的?” 終于他也表示出了一種驚異的表情,舉起了他那兩只朦朧的老在注視鼻尖的眼睛。左手捏住了我的手,右手他就在袋里摸出了一塊黑而且濕的手帕來揩他頭上的汗。 “因為教書教得太起勁了,所以你的上來,我竟沒有聽到。這天氣可真了不得。你的病好了么?” 他接連著說出了許多前后不接的問我的話,這是他的興奮狀態的表示,也還是學生時代的那一種樣子。我略答了他一下,就問他以后有沒有課了。他說: “今天因為甲班的學生,已經畢業了,所以只剩了這一班乙班,我的數學教完,今天是沒有課了。下一個鐘頭的英文,是由校長自己教的。” “那么我們上湖濱去走走,你說可以不可以?” “可以,可以,馬上就去。” 于是乎我們就到了湖濱,就上了這一家大約是第四五流的小小的飯館。 在飯館里坐下,點好了幾盤價廉可口的小菜,楊梅燒酒也喝了幾口之后,我們才開始細細的談起別后的天來。 “你近來的生活怎么樣?”開始頭一句,他就問起了我的職業。 “職業雖則沒有,窮雖則也窮到可觀的地步,但是吃飯穿衣的幾件事情,總也勉強的在這里支持過去。你呢?” “我么?像你所看見的一樣,倒也還好。這暑期學校里教一個月書,倒也有十六塊大洋的進款。” “那么暑期學校完了就怎么辦哩?” “也就在那里的完全小學校里教書,好在先生只有我和校長兩個,十六塊錢一月是不會沒有的。聽說你在做書,進款大約總還好吧?” “好是不會好的,但十六塊或六十塊里外的錢是每月弄得到的。” “說你是病倒在上海的養老院里的這一件事情,雖然是人家的假冒,但是這假冒者何以偏又要來使用像你我這樣的人的名義哩?” “這大約是因為這位假冒者受了一點教育的毒害的緣故。大約因為他也是和你我一樣的有了一點知識而沒有正當的地方去用。” “曖,曖,說起來知識的正當的用處,我到現在也正在這里想。我的應用化學的知識,回國以后雖則還沒有用到過一天,但是,但是,我想這一次總可以成功的。” 談到了這里,他的顏面轉換了方向,不在向我看了,而轉眼看向了外邊的太陽光里。 “曖,這一回我想總可以成功的。” 他簡直是忘記了我,似乎在一個人獨語的樣子。 “初步機械二千元,工廠建筑一千五百元,一千元買石英等材料和石炭,一千元人夫廣告,曖,廣告卻不可以不登,總計五千五百元。五千五百元的資本。以后就可以燒制出品,算它只出一百塊的制品一天,那么一三得三,一個月三千塊,一年么三萬六千塊,打一個八折,三八兩萬四,三六一千八,總也還有兩萬五千八百塊。以六千塊還資本,以六千塊做擴張費,把一萬塊錢來造它一所住宅,曖,住宅,當然公司里的人是都可以來住的。那么,那么,只教一年,一年之后,就可以了。……” 我只聽他計算得起勁,但簡直不曉得他在那里計算些什么,所以又輕輕地問他: “你在計算的是什么?是明朝的演題么?” “不,不,我說的是玻璃工廠,一年之后,本利償清,又可以拿出一萬塊錢來造一所共同的住宅,呀,你說多么占利啊!曖,這一所住宅,造好之后,你還可以來住哩,來住著寫書,并且順便也對以替我們做點廣告之類,好不好,干杯,干杯,干了它這一杯燒酒。” 莫名其妙,他把酒杯擎起來了,我也只得和他一道,把一杯楊梅已經吃了剩下來的燒酒干了。他干下了那半杯燒酒,緊閉著嘴,又把眼睛閉上,陶然地靜止了一分鐘。隨后又張開廠那雙紅腫的眼睛。大聲叫著茶房說: “堂倌,再來兩杯!” 兩杯新的楊梅燒酒來后,他緊閉著眼,背靠著后面的板壁,一只手拿著手帕,一次一次的揩拭面部的汗珠,一只手盡是一個一個的拿著楊梅在對嘴里送。嚼著靠著,眼睛閉著,他一面還盡在哼哼的說著: “曖,曖,造一間住宅,在湖濱造一間新式的住宅。玻璃,玻璃么,用本廠的玻璃,要斯斷格拉斯。一萬塊錢,一萬塊大洋。” 這樣的哼了一陣,吃楊梅吃了一陣了,他又忽而把酒杯舉起,睜開眼叫我說: “喂,老同學,朋友,冉干一杯!” 我沒有法子,所以只好又舉起杯來和他干了一半,但看看他的那杯高玻璃杯的楊梅燒酒,卻是楊梅與酒都已吃完了。喝完酒后,一面又閉上眼睛,向后面的板壁靠著,一面他又高叫著堂倌說: “堂倌!再來兩杯!” 堂倌果然又拿了兩杯盛得滿滿的楊梅與酒來,擺在我們的面前。他又同從前一樣的閉上眼睛,靠著板壁,在一個楊梅,一個楊梅的往嘴里送。我這時候也有點喝得醺醺地醉了,所以什么也不去管它,只是沉默著在桌上將兩手叉住了頭打瞌睡,但是在還沒有完全睡熟的耳旁,只聽見同蜜蜂叫似的他在哼著說: “啊,真痛快,痛快,一萬塊錢!一所湖濱的住宅!一個老同學,一位朋友,從遠地方來,喝酒,喝酒,喝酒!” 我因為被他這樣的在那里叫著,所以終于睡不舒服。但是這伏天的兩杯楊梅燒酒。和半日的火車旅行,已經弄得我倦極了,所以很想馬上去就近尋一個旅館來睡一下。這時候正好他又睜開眼來叫我干第三杯燒酒了,我也順便清醒了一下,睜大了雙眼,和他真真地干了一杯。等這杯似甘非甘的燒酒落肚,我卻也有點支持不住了,所以就教堂倌過來算帳。他看見了堂倌過來,我在付帳了,就同發了瘋似的突然站起,一只手叉住了我那只捏著紙幣的右手,一只左手盡在褲腰左近的皮袋里亂摸;等堂倌將我的紙幣拿去,把找頭的銅元角子拿來擺在桌上的時候,他臉上一青,紅腫的眼睛一吊,順手就把桌上的銅元抓起,鏘丁丁的擲上了我的面部。“撲搭”地一響,我的右眼上面的太陽穴里就涼陰陰地起了一種刺激的感覺,接著就有點痛起來了。這時候我也被酒精激刺著發了作,呆視住他,大聲地喝了一聲: “喂,你發了瘋了么,你在干什么?” 他那一張本來是畸形的面上,弄得滿面青青,漲溢著一層殺氣。 “操你的,我要打倒你們這些資本家,打倒你們這些不勞而食的畜生,來,我們來比比腕力看。要你來付錢,你算在賣富么?” 他眉毛一豎,牙齒咬得緊緊,捏起兩個拳頭,狠命的就撲上了我的身邊。我也覺得氣極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和他扭打了起來。 白丹,丁當,撲落撲落的桌椅杯盤都倒翻在地上了,我和他兩個就也滾跌到了店門的外頭。兩個人打到了如何的地步,我簡直不曉得了,只聽見四面嘩嘩嘩嘩的趕聚了許多閑人車夫巡警攏來。 等我睡醒了一覺,渴想著水喝,支著鱗傷遍體的身體在第二分署的木柵欄里醒轉來的時候,短短的夏夜,已經是天將放亮的午夜三四點鐘的時刻了。 我睜開了兩眼,向四面看了一周,又向柵欄外剛走過去的一位值夜的巡警問了一個明白,才朦朧地記起了白天的情節。我又問我的那位朋友呢,巡警說,他早已酒醒,兩點鐘之前回到城站的學校里去了。我就求他去向巡長回稟一聲,馬上放我回去。他去了一刻之后,就把我的長衫草帽并錢包拿還了我。我一面把衣服穿上,出去解了一個小解,一面就請他去倒一碗水來給我止渴。等我將五元紙幣私下塞在他的手里,帶上草帽,由第二分署的大門口走出來的時候,天已經完全亮了。被曉風一吹,頭腦清醒了一點(www.lz13.cn),我卻想起了昨天午后的事情全部,同時在心坎里竟同觸了電似地起了一層淡淡的憂郁的微波。 “啊啊,大約這就是人生吧!” 我一邊慢慢地向前走著,一邊不知不覺地從嘴里卻念出了這樣的一句獨白來。 一九三○年八月作 (原載一九三○年七月一日《北新半月刊》第四卷第十三號(該刊此期衍期。——編者注),據《達夫短篇小說集》下冊) 郁達夫作品_郁達夫散文集 郁達夫:春風沉醉的晚上 郁達夫:陽光廣場分頁:123
如何讓同事看到你的光彩 我有一個怯生生的實習生,一提到開會,她就不知道自己該不該去,大家的討論一激烈,她就完全插不上話。有一次在會議中,她悄悄發短信給我說:“要不我先回去吧,等你們說完了,告訴我怎么做就好了。”我回復她:“你必須在,否則更沒人看到你。” 初來乍到的實習生,總會遇到這樣的情況:左看看右看看,光鮮亮麗的公司里,哪里都有前輩們閃爍的身影。低頭看看自己,總覺得衣服也土土的,講話也弱弱的,開會更是不敢發言,仿佛只有發快遞和訂盒飯的時候才能體現出自己的存在。難道這就是實習的意義嗎? 說到底,實習生剛剛進入公司的時候,不要太著急出頭。現在的職場雖然不會像傳說中那么槍打出頭鳥,但急于表現自己并不是一件受歡迎的事情。就算要出頭,一定記住要通過能力,而不是通過走路使勁兒扭腰,沒事打小報告以及在公司里傳八卦鬧緋聞的方式。 年輕是一種資本,而資本用對了地方才能得人心。職場是一個需要自己表現才能被別人看見的地方,因此,不能總躲著當一棵無名小草。實習生什么都不會,如何能在短時間內讓自己的能力提升,靠實力說話?如何讓大家看見自己的才能? 日常工作中,實習生干得最多的一定是發快遞、填表格這類事情。你有沒有想過,這里面也有學問。比如發重要的快遞之前,保價或者選用最可靠的快遞公司?之后是否與對方聯系,確認收到并告知領導?填表格時是否留意過,你交給領導的格式和領導交給客戶的格式是否不同?所謂亮點,并非一定要做轟轟烈烈的大事,當一些日積月累的小事讓同事放心的時候,當領導漸漸交給你更多任務,而不再緊盯著你問結果的時候,你就慢慢開始發光了。 至于開會發言,這里面就更有學問了。一般開會之前,會議召集人都會用郵件發出邀請并列出會議的主要內容。即使沒有邀請,領導也會提前通知什么時候要開什么會,讓大家準備一下。想想每次你是提前認真準備,還是腦子一片空白地走進會議室,進門就悶頭聽大家說?事實證明,無論是誰,在頭腦風暴中作出精彩發言,都是最好的讓大家認識你的方式。你可以提前熟悉會議內容并盡力準備,討論時積極說出自己的想法。 可能有時候你會覺得自己的想法有些幼稚,或者大家把你想說的提前說了,因此就更要多考慮一些不同的角度,或者早一點發言。如果實在講不出什么,那就認真做會議記錄吧。有條理地記錄下大家的想法和意見,會后整理好發給大家,一定會讓同事們覺得,你是個靠譜兒的年輕人。 不過,不管是哪種方法,首先是你一定要先做點什么。前面提到的那個實習生,現在可是我的得力干將,盡管她還沒畢業,但日常做的文案已經可以直接發給客戶了。因此在開會的時候,我都會讓她發言,直接講她寫的部分。有時候她還會挖掘出一些新的內容和想法與大家分享,這讓我特別愿意在合適的場合把她介紹給大家。 10個小細節,毀掉同事對你的好印象 求職面試的十大秘籍 求職面試的八大禁忌分頁:123
ACC711CEV55CE



 留言列表
留言列表


